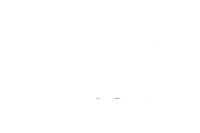伯大尼耶瑟
我的名字叫贝瑟妮-叶泽尔(Bethany Yeiser),感谢氯氮平让我在过去的 15 年里从精神分裂症中完全康复。在我第一次入院两天后,我的父母被告知我已经永久性完全残疾。但如今,我已完全康复。
我的历史和康复
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父母关爱我、支持我,还有一个比我小一岁半的弟弟。我在高中茁壮成长,我的爱好是小提琴。13 岁时,我开始每天练习四小时,加入了克利夫兰管弦乐团青年交响乐团,并被克利夫兰市中心一所音乐学院的教授录取为小提琴学生。
当我考虑大学的时候,我的首选是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USC)。当我前往那里参观时,突然感觉整个世界都向我敞开了怀抱。我可以成为遗传学家、工程师、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当南加州大学为我提供半额奖学金时,我被录取了。我的新梦想正在展开。
在我开始南加州大学课程的前一个暑假,一位家庭朋友安排我到一个医学研究实验室做志愿者,主要研究抗生素耐药性。那个暑假,我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两本期刊上,我也是其中的作者之一。
1999 年秋天,17 岁的我离开俄亥俄州前往南加州大学。到校不久,我就有幸成为社区管弦乐队的首席。我报名参加了具有挑战性的课程。我还开始与一位科学家合作,他发现了一种容易出错的 DNA 聚合酶(DNA 复制器)。易出错的 DNA 聚合酶后来在人类身上被发现,并与某些类型的癌症有关。
我记得每周五下午都要参加实验室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教授解释说,如果某个实验能带来另一个理想的结果,从而带来另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诺贝尔奖就指日可待了。
我相信实验室里的每个人都不会理会这些评论,因为它们不切实际。但它们却成了我的世界。这是开始漫长妄想之旅的第一个火花。
在南加州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放弃了管弦乐队首席的职位,一有空就泡在实验室里。最后,我发现自己经常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出乎意料的是,我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非常有希望的发现,那就是某种容易出错的DNA复制器的重要性,然后我就梦想着能在该领域最好的期刊上发表我的研究成果。
第一学期,我的成绩几乎是全 A,而且我觉得我的课程比预期的要简单,但在第二学期,我的成绩下滑了,因为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里。我记得大一第二学期的生物课得了 C-,因为这门课涉及的生物知识我在实验室里没有接触过。当我沉迷于实验室时,我忘记了自己的重点。
2001 年大三刚开学时,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我的世界开始变得不同。当时,我开始思考,我是否可以为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挣扎者提供基本生活所需资金,并以某种方式为实现世界和平而努力,从而对全世界产生影响。
那个学期,我所在的教会派出了一支由女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组成的队伍,其中包括我,前往中国探访穷人。 在中国昆明着陆后,我和这群年轻女性来到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我记得当时我在想"我能帮助中国一百万贫困人口吗?""我能帮助数百万人吗?"突然间,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目标,我确信,是的,影响世界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后,我意识到这是我最初的错觉之一。
从中国回来后,我就燃起了去非洲--特别是去一个贫民窟地区看看的念头。我决定在接下来的暑假独自前往非洲。我的父母对我的决定感到非常不安和担心。我答应向他们提供我的联系方式,但在非洲期间,我为没有照顾好自己而感到内疚,我也害怕父母会专程到肯尼亚来找我。我在贫民窟没有住址,也没有给我父母一个非洲女人的电话号码,而这个女人本可以帮他们找到我。我在非洲待了两个半月。最后一个月,在离开这个国家之前,我在尼日利亚待了一个星期,拜访了一位著名的商人和他的妻子。
回到南加州大学后,我重新下定决心要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于是搬进了宿舍,买了课本,认真听讲。我记得第一次考试是在一门高级分子生物学课上。我以为自己考得很好,我很高兴自己又回到了成绩优异的 "正常的自己"。然而,当考试成绩发回给我时,我发现我不及格了,因为我的所有答案都是胡言乱语。
我的思绪像被损坏的黑胶唱片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跳回到同一个地方。我发现,除了非洲,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无法继续前行。当时,尽管学业失败,我还是与一位朋友合作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称之为 "创新医学国际"。通过这个组织,我筹集到了数千美元,并寄给了我在非洲结识的朋友。
几个月后,我正式从南加州大学退学,搬出宿舍,开始睡在学校图书馆里。由于精神崩溃,我完全无法学习或工作。我完全失去了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我的父母试图联系我的教会、朋友和教授,试图与我取得联系,但我坚决拒绝了任何联系。他们给我寄来了一个大包裹,我拒绝了,并将包裹退还给了他们。他们提出让我用他们的信用卡支付基本的生活费用和食物。我拒绝了。我担心他们会以某种方式阻止我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因为我有一张南加州大学的身份证,而且看起来还在有效期内,所以我没有被要求离开图书馆,就这样我在夹缝中溜达了两年半。我还开始和那些经常在图书馆通宵学习或编写计算机代码的学生交朋友。我成了在公共浴室洗漱和在凌晨两三点寻找废弃食物吃的专家。
在我无家可归的头三年,妄想症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继续对父母疑神疑鬼。我并没有意识到精神分裂症已经占据了我的生活,因为我的行为还没有离奇到足以被警察发现的地步。
2006 年 1 月 28 日,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突然听到一些声音,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些声音其实是来自我自己的心灵。很快,我又听到了更多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群年轻学生的合唱。接下来是视觉幻觉。我记得自己照镜子时看到的是自己的倒影,但看到的却是我的脸和 "辛普森一家 "中的人物丽莎的交叉图像。
声音一开始出现,我就放弃了躲在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开始住在外面。在大学附近的一个教堂院子里的第一个晚上,我穿了三件换洗衣服,层层叠叠,以保持温暖。几个月后,当我再次非法闯入南加州大学校园时,被警察抓了起来,关了两天,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监狱里拥挤不堪,光线昏暗。出院后,我出现了指令性幻觉,让我尖叫并大声辱骂。2007 年 3 月 3 日,我再次被警察带走,这次我被带到精神病院进行评估。
当我被送进急诊室进行精神评估时,我的父母接到了通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找我谈话,因为我已经从大学辍学,无家可归。但我还是同意和妈妈谈谈。在电话中,我注意到她说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 "你可能是 "或 "你曾经是",而是 "你是"。她说她很想我。我的父母在 24 小时内赶到了医院。他们的同情打动了我的心。
我坚持认为自己不需要抗精神病药物,但几天后,我同意开始服用利培酮。利培酮的疗效让人惊叹。视幻觉消失了。对父母和朋友的妄想症几天后也消失了。我的许多幻听和幻视也消失了。但是,即使我的严重症状消失了,我仍然能在脑海中听到响亮的声音,就像收音机在不同频道之间播放一样,我从不相信我生病了或者正在好转。
没有人指出我的治疗团队注意到利培酮的积极作用。我不记得有人告诉过我我的诊断,也不记得我可能会遇到什么副作用。我不知道还有其他药物可以尝试。一位工作人员简单地告诉我,我可能会终生服用这种药物。同时,我也不相信自己需要这种药物。我相信他并不了解我,或者是被我弄糊涂了。
住院两周半后,我和父母一起飞回俄亥俄州南部的家中休养。我在加利福尼亚时,他们已经从克利夫兰搬到了辛辛那提。我父母的朋友们对我慷慨大方、和蔼可亲,从不过问我之前五年的生活是如何度过的。
然而,当我到了俄亥俄州后,利培酮的副作用成了问题。我每天要睡 16-18 个小时,在医院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以为自己只是因为无聊才休息的。我的肌肉变得越来越僵硬,并出现了无运动症状,即极度不安。我的情感变得迟钝(情绪表达平淡),无法欣赏自己喜欢的音乐或图片,因为药物削弱了我体验快乐的能力。没有快感,或者说 "失乐症",是最让我困扰的副作用。我的食欲也无法控制,体重很快就增加了近 20 磅。
我对自己的身份很自信,确信自己不需要抗精神病药物,也不知道药物对自己有什么帮助,于是我停用了利培酮。几天后,我开始嚷嚷着要回加利福尼亚。停药后,我只想再次无家可归,重获 "自由"。我又一次陷入了幻觉和躁动的花癫状态,最后还摔坏了一把昂贵的小提琴。我们家的一位朋友拨打了 911,请求对我的病情进行医疗干预,我再次被送进了医院。
在我第二次住院期间,一位精神科医生给了我一条生路。他说:"你还记得自己拉过高水平的小提琴 学过分子生物学吗?"他说,我也许可以重新拥有这些东西,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一直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他还告诉我,每次重新开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即使剂量再大,效果也会变差,停药最终会导致残疾。我认为,每个病人在开始服药的那天都应该被告知这一点。
大约五天后,我离开了医院,现在我知道自己一直需要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虽然是不同的药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感觉自己就像过去的影子。我无法上学、工作,甚至无法参加有意义的志愿活动。我的生活就是睡觉、休息和倾听心中的声音。我像一个完全残疾的人一样生活了 12 个月,甚至还要忍受各种抗精神病药物的折磨。
当时,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了,我被介绍给一位名叫亨利-纳斯鲁拉(Henry Nasrallah)的精神分裂症专家。从一开始,纳斯鲁拉医生就与我合作过的其他精神科医生不同。他仔细查阅了我的人生成就史,包括我在克利夫兰实验室和南加州大学发表的三篇科学论文。他知道我曾经拉过高水平的小提琴。他还知道我想完成分子生物学学位,但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
纳斯鲁拉医生让我开始服用氯氮平这种我从未听说过的药物。纳斯鲁拉医生告诉我氯氮平的潜在副作用,包括体重增加、镇静,以及需要每周抽血检查白细胞计数。
服用氯氮平一个月后,我看到了真正的进步。我的幻听明显减少,这是我服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所没有的。大约六个月后,我的病情完全缓解。我与纳斯拉拉医生就我的未来目标和计划进行了多次长谈。他鼓励我重新注册并完成大学学业。
2009 年,在开始服用氯氮平一年半之后,我从辛辛那提郊区的父母家搬到了离辛辛那提大学步行几分钟的公寓里。2011 年 12 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从辛辛那提大学分子生物学专业毕业。我的父母和纳斯鲁拉博士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他们的心情非常激动。
与医生和家人分享
大学毕业后,纳斯鲁拉博士鼓励我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我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了回忆录,并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人生》的书。 心灵疏远:我从精神分裂症和无家可归到康复的旅程.我妈妈还以母亲和护士的视角写了一本配套书籍。她的书名是 逃离理性:一位母亲关于精神分裂症、康复和希望的故事.这两本书均于 2014 年夏天出版。
在出版了 心灵疏远、 我开始四处奔波,向患者家属和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介绍如何通过坚持服药以及对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氯氮平治疗来实现持续、全面的康复。通过这些交流,我了解到,家人常常被告知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康复的希望。我也经常遇到一些医生,他们也认为精神分裂症不可能痊愈,甚至从未考虑过使用氯氮平来治疗那些服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
我的宣传活动的亮点之一是会见了一位医生,他听了我使用氯氮平康复的故事后,决定彻底改变他的做法--绝不放弃他的病人,并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氯氮平。这位医生现在是我们 CURESZ 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我开始了新的写作生涯,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表演讲,最初是与纳斯鲁拉博士一起参加医学会议,后来则是自己一个人。我发现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并感到自己在改变重症精神病患者的生活。如今,我头脑清醒,生活有了目标。
成立 CURESZ 基金会
2016年,纳斯拉拉博士向我提出了另一个想法,那就是成立一个非营利性基金会,我们称之为 "通过研究和教育全面了解精神分裂症",缩写为CURESZ。现在,CURESZ 基金会为数千个有亲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家庭提供服务。CURESZ 计划包括我们的照顾者指导计划、支持小组、问医活动和校内俱乐部。这些计划将在 觉醒 我们还为第二部分中介绍的 "幸存者 "感到骄傲,他们在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下依然茁壮成长。
多年来我认识到,精神科医生永远不要放弃与精神分裂症作斗争的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永远不要失去希望或放弃自己,这一点至关重要。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位精神科医生在认识我两天后就告诉我的父母,我是永久性完全残疾。
对于像我这样的耐药性患者来说,氯氮平是最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但却是一种未被充分利用的药物选择。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失败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至少每 3 人中就有 1 人符合使用氯氮平的条件,但在美国,每 25 人中只有 1 人真正得到了这种药物的处方。这意味着,美国有成千上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持续的妄想和幻觉而致残,在许多情况下是完全致残,而他们甚至从未听说过氯氮平。氯氮平有可能消除他们的精神病,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恢复到健康的基线,就像我一样。
2018 年,CURESZ 基金会成立了一个氯氮平专家小组,帮助家庭找到 CURESZ.org 上显示的就近开具氯氮平处方的医生。
在我继续生活的过程中,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拒绝放弃我,即使我生活中的其他人都放弃了我。我还要感谢我的前任精神病医生和《我的人生》一书的作者之一。 觉醒 亨利-纳斯鲁拉博士。他毕生致力于帮助像我这样被许多临床医生遗忘、忽视、拒绝或认为无药可救的人。
通过我在《世界文化论坛》第一部分中撰写的文章 觉醒通过这个个人故事,我想申明,我并不认为我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是一个无期徒刑或永久性残疾。多亏了我坚持服用氯氮平,以及家人、朋友和纳斯拉拉医生的支持,我才得以康复。如今,我过着非常快乐、忙碌和充实的生活。
我坚信我的未来是光明的。今天,我很荣幸并谦卑地担任 CURESZ 基金会主席,每天花几个小时来执行基金会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