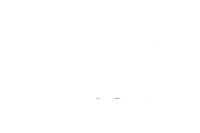该图像名为“The WXYZ”,由 Tung Ken Lam 设计,由 Joy 折叠。
克服分裂情感障碍:乔伊·伊莎贝尔
我在俄亥俄州长大,在慈爱的父母身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我参与了许多活动,包括舞蹈、越野、乐队和教堂。然而,我记得早在二年级时就有过剧烈的情绪波动。它们影响了我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但我的情绪波动并未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征兆。
2003 年,我高中毕业,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希望在那里结识终生挚友。在纯粹的社交场合与人互动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个非常大的大学结构松散的环境中,我很难交到亲密的朋友。
直到 20 多岁开始读研究生时,我的情绪状态才变得难以忍受。我忍不住哭了。最后,在 2010 年,我去看了一位心理咨询师,他认识到我的抑郁症并推荐了团体治疗。几个星期以来,我参加了短期团体治疗,这确实让我感觉好多了。不幸的是,当我每天都在与自己的情绪作斗争时,我的幻想破灭了。
我坚持学习,并于2013年获得了英语教学硕士学位。我希望如果我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就能长期坚持下去。在我十几岁和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做过很多工作,但大多数工作都无法保住一两年以上。有时工作压力很大,有时我只是挣扎,因为社交互动很困难。
于是,手握学位,心存希望,我于2013年离开中国去中国教英语。体验一个新的国家和文化,我飞得很高,实现了我的梦想,享受着我的生活。
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在中国变得更加孤立。我的孤独终于把我推到了边缘。我很偏执,患有严重的焦虑症。妄想,我失去了应对、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在我的妄想世界里,我以为我要被陷害犯罪,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所以我做出了自残行为,并狂热地自杀。
从中国回来后,我逃离了家人,开始流落街头,经历饥饿、疾病和消瘦。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经历是我内心深处的恐惧。当我允许自己再次开始进食时,我的情绪开始好转,但我仍然有错觉。我的信念是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帮助或去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所以我吃垃圾箱。这段时间,我拒绝和父母联系。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怕我不是死了就是怕我有大麻烦。我的父母竭尽所能找到我。直到他们后来收到我的急诊室账单,他们才找到我,我们才重新团聚。
当我在街上流浪几个月后决定去医院时,就产生了急诊室的费用。一位好心的警察在高速公路边上接我,然后把我送到医院。虽然我最初不相信自己患有精神病,但我确实意识到自己病了。我乐于了解自己的病情,被诊断为分裂情感障碍,双相型。直到今天,我从 2016 年底开始一直吃药。
但即使在我住院几年后,我仍然患有偏执狂和焦虑症,无法出门、与朋友共度时光和找工作。终于,在 2018 年年中,我找到了一份销售职位,开始每周工作 40 小时。我的工作给了我一种常态感和自我价值感,我现在比开始工作前更健康。
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工作和通勤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让我感到疲倦,但我仍然能够进行自我保健。
定期锻炼和跑半程马拉松让我保持健康并增加我的内啡肽。参加当地的折纸小组提供了一个支持性的学习和教学环境。针织、钩编和缝纫衣物和毯子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出口,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园艺和庭院工作让我与大自然保持接触,并提供一种幸福感。
住在家里,我得到了父母的情感支持,他们看到我在流浪者收容所还活着,感到很欣慰。他们很高兴我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并且支持我的康复和自我保健的努力。
我还受益于参加当地的精神分裂症匿名者 (SA) 会议,在那里我结识了朋友,并可以与了解我患有精神病的日常经历的人互动。我已经参加 SA 几个月了。
每个人和每种情况都不同。对我来说,工作一直在治愈,帮助我从疾病中康复。如果你想工作,我鼓励你寻找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并尝试。你可能会发现它给你带来了美好的世界。